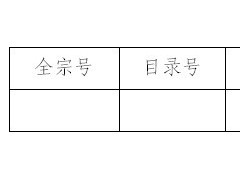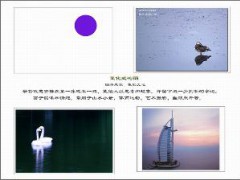中國(guó)明代以前對(duì)檔案的稱呼與文書(shū)不加區(qū)分,有典、冊(cè)、策、中(冊(cè)字的省形)、簡(jiǎn)牘、文書(shū)、簿書(shū)、案卷、文案、案牘等稱謂。
“檔案”一詞始見(jiàn)于清代,康熙十九年(1680年)《起居注》中記載,康熙帝在披閱秋審眾犯冊(cè)時(shí)問(wèn):“馬哈喇之父與叔皆沒(méi)于陣,本人亦有功牌,其罪如何?”大學(xué)士奏曰:“部中無(wú)檔案,故控告時(shí)部議不準(zhǔn)。”大約成書(shū)于康熙四十六年的楊賓《柳邊紀(jì)略》則對(duì)檔案有所解釋?zhuān)骸斑呁馕淖侄鄷?shū)于木,往來(lái)傳遞者曰牌子,以削木若牌故也;存儲(chǔ)年久者曰檔案,曰檔子,以積累多貫皮條掛壁若檔故也。”清入關(guān)后改用紙張書(shū)寫(xiě),但習(xí)慣相因,仍將保存起來(lái)的文書(shū)稱作“檔案”、“檔子”。在其后的律令條例中,對(duì)于“文書(shū)”和“檔案”的用法,更有較為明確的區(qū)分,多處使用“繕寫(xiě)文書(shū),收貯檔案”,“錄存檔案”,“檔案副本”等等。
按漢字本義,“檔”為橫木框格,系指存放東西的閣架;“案”即小桌子一類(lèi)的東西,引伸為處理某一事件的案卷。“檔案”即存入檔架的案卷,沿用至今仍有其形象的和內(nèi)在的意義,并賦予了新的科學(xué)含義。
歐美諸語(yǔ)言中檔案一詞均源于希臘文αρχειον和拉丁文archivum,文字和發(fā)音都很相近。其原意為行政機(jī)關(guān)所在地,后指保存公務(wù)案卷或其他文件的處所,進(jìn)而兼指保存在這些地方的檔案。它是一個(gè)多義詞,可解為檔案庫(kù)、檔案室、檔案館、檔案等等,因而使用時(shí)往往需要加以限定或說(shuō)明。如俄文архив,在30年代多指檔案館,對(duì)檔案則稱архивныйматериал(檔案材料);近年蘇聯(lián)國(guó)家標(biāo)準(zhǔn)文件規(guī)定以архивныйдокумент(檔案文件)為特指檔案的通用術(shù)語(yǔ)。
在日文的一般詞匯中無(wú)檔案一詞,常用ぶんしよ(文書(shū))或こぅぶんしよ(公文書(shū)),日本國(guó)家檔案館稱為こぅぶんしよかん(公文書(shū)館);而在漢文日譯時(shí)使用とぅぁん(檔案)或とぅし(檔子)。
“檔案”一詞始見(jiàn)于清代,康熙十九年(1680年)《起居注》中記載,康熙帝在披閱秋審眾犯冊(cè)時(shí)問(wèn):“馬哈喇之父與叔皆沒(méi)于陣,本人亦有功牌,其罪如何?”大學(xué)士奏曰:“部中無(wú)檔案,故控告時(shí)部議不準(zhǔn)。”大約成書(shū)于康熙四十六年的楊賓《柳邊紀(jì)略》則對(duì)檔案有所解釋?zhuān)骸斑呁馕淖侄鄷?shū)于木,往來(lái)傳遞者曰牌子,以削木若牌故也;存儲(chǔ)年久者曰檔案,曰檔子,以積累多貫皮條掛壁若檔故也。”清入關(guān)后改用紙張書(shū)寫(xiě),但習(xí)慣相因,仍將保存起來(lái)的文書(shū)稱作“檔案”、“檔子”。在其后的律令條例中,對(duì)于“文書(shū)”和“檔案”的用法,更有較為明確的區(qū)分,多處使用“繕寫(xiě)文書(shū),收貯檔案”,“錄存檔案”,“檔案副本”等等。
按漢字本義,“檔”為橫木框格,系指存放東西的閣架;“案”即小桌子一類(lèi)的東西,引伸為處理某一事件的案卷。“檔案”即存入檔架的案卷,沿用至今仍有其形象的和內(nèi)在的意義,并賦予了新的科學(xué)含義。
歐美諸語(yǔ)言中檔案一詞均源于希臘文αρχειον和拉丁文archivum,文字和發(fā)音都很相近。其原意為行政機(jī)關(guān)所在地,后指保存公務(wù)案卷或其他文件的處所,進(jìn)而兼指保存在這些地方的檔案。它是一個(gè)多義詞,可解為檔案庫(kù)、檔案室、檔案館、檔案等等,因而使用時(shí)往往需要加以限定或說(shuō)明。如俄文архив,在30年代多指檔案館,對(duì)檔案則稱архивныйматериал(檔案材料);近年蘇聯(lián)國(guó)家標(biāo)準(zhǔn)文件規(guī)定以архивныйдокумент(檔案文件)為特指檔案的通用術(shù)語(yǔ)。
在日文的一般詞匯中無(wú)檔案一詞,常用ぶんしよ(文書(shū))或こぅぶんしよ(公文書(shū)),日本國(guó)家檔案館稱為こぅぶんしよかん(公文書(shū)館);而在漢文日譯時(shí)使用とぅぁん(檔案)或とぅし(檔子)。